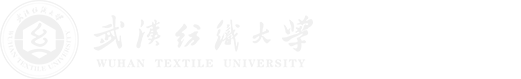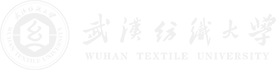在国内伦理学语境中,“社会赏罚”是个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从名称看它似乎是与道德无关,实际上与道德,特别是道德的实现,有着极为密切和至关重要的关联。而以往伦理学也正是由于缺乏对这种关联的关注与揭示,导致在道德建设问题上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以释怀的理论困惑。
“社会赏罚”是社会力量就一些特定行为对行为者做出的奖赏或惩罚。在这个定义中,所谓“社会力量”,既是指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政府和社会机构,也可以是指拥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各类社会组织、群体乃至个人。所谓“特定行为”,是指那些事先已被纳入赏罚范围的行为。至于“行为者”,就是做了“特定行为”的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所有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政府、政府官员等社会公共权力执掌者,都有可能是这样的行为主体。
在现实社会中,以道德为目的的社会赏罚的具体形式虽多种多样,但最终都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方式:让遵从道德者得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令违反道德者不仅得不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甚至还要失去他们不愿失去的东西。举例来说,将以道德为目的的社会赏罚基本方式用于商人,就是让那些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生产销售货真价实商品的商人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市场份额与利润;令那些违法经营,不守诚信、制假售假的商人不仅得不到他们想得到的暴利或高市场份额,而且还要挨罚,失去他们所不愿失去的原有的资质、权利、资产、金钱。
根据对“社会赏罚”的以上理解,应该能够让我们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对任何社会的道德风貌的解释,应当深入到该社会的社会赏罚中去寻找成因。以往我们对道德风貌及社会道德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意识形态、思想教育和文化素质、主观觉悟等方面进行,很少着眼于社会赏罚机制,结果所得结论不仅缺少说服力,而且往往于事无补。譬如腐败,倘若我们无法从制度上有效预防、及时惩处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的行为,就是进行再多的道德说教,也无法真正遏制愈演愈烈的腐败。这就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此推广可知,一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或道德滑坡,可能与总体性社会赏罚机制的倒置有关。总之,虽然人们的行为会受来自各方的思想、文化观念及道德观念的影响,但体现整个社会道德风貌的大众行为,最终却只受他们所处的社会中的社会赏罚机制的支配。因此,我们只有深入到社会总体赏罚机制中去做全面的剖析,才会为社会道德风貌及各种社会道德问题找到真正的成因和有效的疗法。
启示二:在整个道德文化的建设中,道德规范的设计和道德教育只是道德文化建设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内容,如果没有社会赏罚机制的配合,任何道德规范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社会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括道德规范设计,道德宣传教育和社会赏罚构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三项内容的建设中,相对而言,道德规范设计并不太难,道德宣传教育也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人们在了解道德规范之后将其付诸于自己的行动,这就取决于能否建构起总体社会赏罚机制与之配套。有关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体认:商人不得制假售假,医生不得收病人红包,公务员不得贪污腐败,是早已有之的底线道德要求和制度规定,也早已为人们广泛知晓。不仅如此,对违反这些规定的不良行为,社会管理者还不断从制度层面想出种种举措加以防范、惩治,可时至今日这些规定仍被不断违反。个中原委,就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相关社会赏罚机制与这些规定配套,尤其是没能找到普遍有效的监督方式,致使这些领域中的众多违法乱纪者能够逍遥法外。由此可见,道德规范设计只能算道德建设的开始,道德教育只能算道德建设的起步,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此后有没有对相应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的选择与建构。
启示三:在以往的经济改革和官员考量中,如“价格双轨制导致寻租效应”、“只重上报数字导致数字干部”等现象告诉我们,出于非道德目的而实施的制度安排,客观上往往也具有道德调控的作用,会结出或甜美或苦涩的道德果实。因而在做这样的制度安排时,社会管理者不仅要考虑其是否有利于实际工作目标的实现,也应自觉进行道德方面的考量,看其是否也有利于社会的道德建设。(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